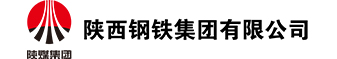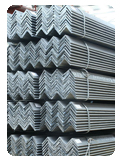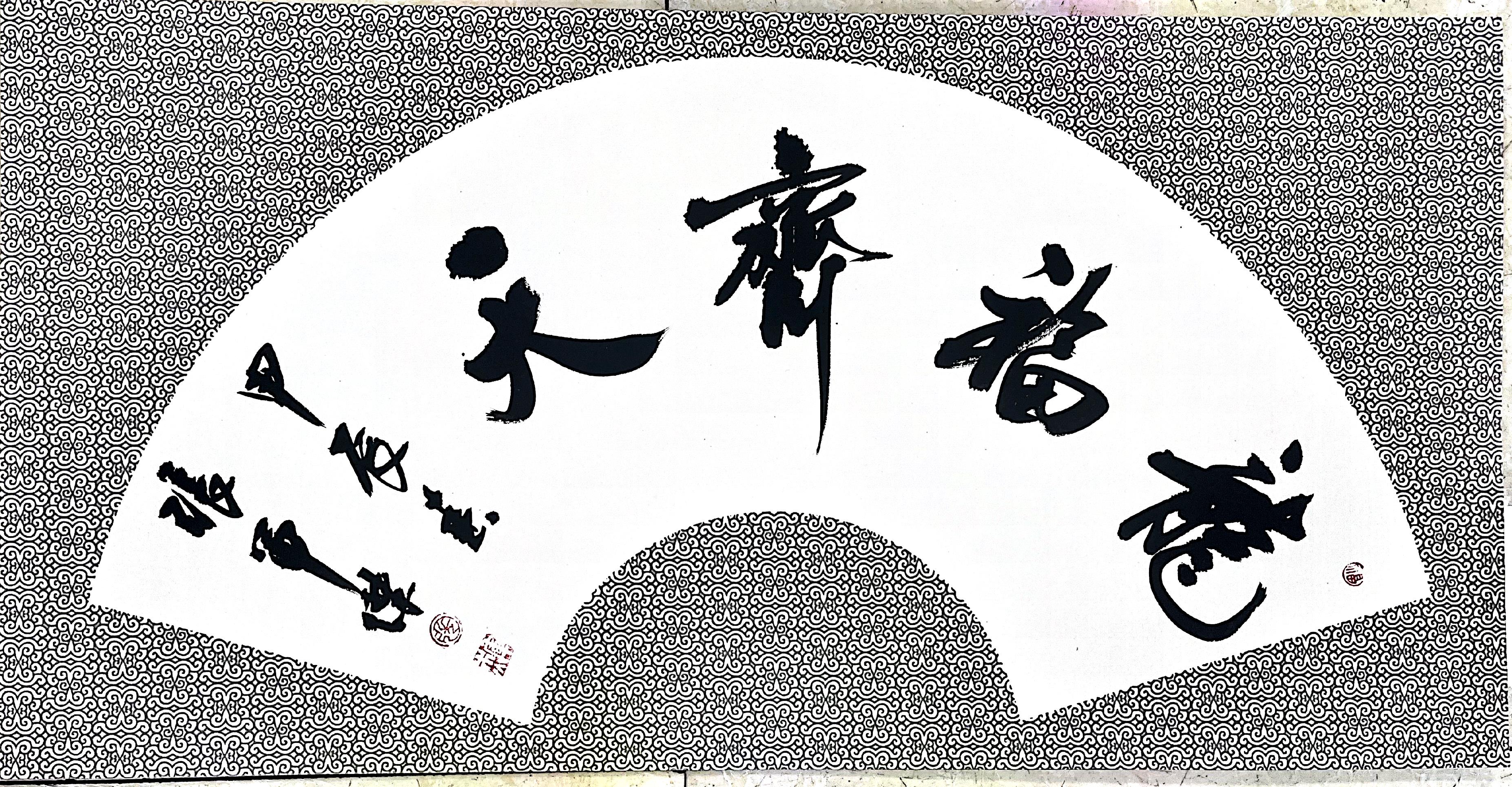父親是陜北人,少年時便離了故土,只身漂泊在外。他像一粒被風吹散的種子,落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根發芽。故鄉的黃土地在他骨子里刻下了倔強的印記,可生活的重擔又將他推向遠方。他常說:“人這一輩子,就像黃河里的泥沙,被水沖著走,可最后沉在哪,還得看自己的分量。”
他每年歸家的次數寥寥,可每次回來,我們姐妹幾個總會圍上去,像圍繞一塊突然落地的巨石,既歡喜又怯然。父親身材魁梧,臉上的線條如家鄉山嶺的輪廓,溝壑分明。歲月在他額頭上犁出深深的皺紋,每一條都藏著說不盡的故事。他的手掌寬厚粗糙,指節突出,像老樹的根瘤,那是常年勞作留下的印記。
父親總愛在晚飯后搬了藤椅坐在庭院當中。夏夜的蟬鳴聲中,他點燃一支煙,在明明滅滅的火光里,給我們講些人生道理。他說做人要像老榆樹,經得起風吹雨打;說做事要像黃河水,認準了方向就一股勁往前奔。我們似懂非懂地聽著,只覺得那些話語像夜風中的火星,明明就在眼前,卻怎么也抓不住。
記得有一年臘月,大雪封山。父親踩著厚厚的積雪走了十幾里山路回家,肩上扛著個鼓鼓囊囊的編織袋。進門時,他的棉襖上結了一層薄冰,眉毛胡子都掛著白霜。他從袋子里掏出幾個紅艷艷的蘋果,在昏暗的煤油燈下,那紅色亮得晃眼。我們饞得直咽口水,小手剛要伸過去,父親卻搖搖頭,從腰間摸出一把小刀。他粗糙的手指捏著蘋果慢慢轉動,刀尖在果皮上游走。削下的果皮連成長長的一條,打著旋兒垂下來,像正月里舞動的紅綢。最后遞到我手里的,竟是一只栩栩如生的小白兔,兩只耳朵支棱著,憨態可掬。我捧著這個神奇的禮物,感覺父親那雙能掄起鐵錘的手,原來也能變出這樣的奇跡。那是我童年里無法忘卻的回憶。
現在長大了,和父親卻不似以前親近了,偶爾相視,目光交接,總有些彼此躲閃的陌生。童年時他寬厚的手掌曾是我搖晃學步的穩固支點,如今那雙手,卻似乎只在手機屏幕的光暈里偶爾閃現,隔著千山萬水的信號,彼此問候也只剩下簡明扼要的字節。
前些日子,媽媽不知從哪里找的一個鐵盒子,打開后,里面躺著一沓厚厚的相片,相片有黑白、有彩色的。有我和姐姐幼時騎在父親肩頭,他年輕的臉上笑容舒展,背景是早已拆除的那口老井。畫面悄然流轉,下一張是小學畢業典禮,我穿的花花綠綠,父親牽著我的手,他嘴角微抿,眼神卻很慈祥。再一張,是大學入學,火車站洶涌的人潮里,他緊抿著唇,手臂卻固執地擋開擠向我的人群,側臉繃緊的線條像沉默的堤壩…
照片無聲地流淌,像一條隱秘的時間之河。我從未知曉何時收集、掃描了這些早已泛黃或塵封于舊的影像碎片。一張張,一幕幕,全是我們成長的軌跡,而他的身影,在每一幀的邊角處,像一道恒定而模糊的背景光,始終存在,卻又悄然退后。
我忽然釋懷了,女兒和父親長大后的疏遠其實并不是真正的疏遠,而是我們都將愛藏在了心里。父親的愛,早已從笨拙的言語和刻意的靠近,蛻變成這靜默的、恒常的注視。
思緒流轉間,我想起了父親以前坐在院子里抽煙的樣子。月光給他的輪廓鍍了層銀邊,煙頭的火光忽明忽暗,像顆不肯熄滅的星星。他的沉默里有種力量,就像陜北的黃土高原,看似貧瘠,卻能長出最頑強的生命。
原來父愛就是這樣,它不喧嘩,自有聲;不張揚,自有光。它像故鄉的群山,永遠站在那里,等你回頭時,發現它一直都在。